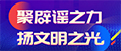◎流年碎影
□王继山
祖籍栾城西宫村,在城南。
城内老宅,在南门里。
父亲的“昇恒義”字号,在南关。
原来是个“馋嘴状元”
夏秋之交的一个夜晚,满天星斗,庭院里静极了,东厢房台阶下那棵茶树,今年叶子很稠,一簇簇小白花散发着幽香。
父亲从柜上回来,便进了北屋。
姥姥不让我进北屋。母亲躺在北屋里间好多天了。
不一会儿,父亲从北屋出来,端着他的宜兴壶,在台阶下花池旁,拉把藤椅坐下喝茶。我在一边儿坐个小板凳儿,仰头数星星。
姥姥哄着大妹,在南屋睡下。父亲让我去东屋睡,我不去。这时,小姨领着一位陌生大婶走进庭院。这人看见父亲,恭敬地叫了一声“二东家”,便相随小姨进了北屋。我问父亲,这人是谁?父亲说,收生婆。我问,什么是收生婆?父亲说,你该去睡了。
满天星星数不清。我歪在躺椅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,我家添了一个胖娃娃。
这年,岁在丁丑,弟弟属牛。
冬去春来,又到夏秋,弟弟一周岁了,长得又白又胖,浓眉毛,大眼睛,比我俊。小姨当着众人,冲我说,比下去了吧!
弟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。
大妹内秀,平和;小妹灵巧,嘴快。“昇恒義”账房王先生,是个爱说爱笑的好老头儿,见了我家小妹就喊:小刁儿;说,长大了给你寻个刁婆婆。小妹听出这不是一句好话,跳着脚打他。姥姥说,该打。大辈儿没个大辈儿样儿……
小姨教大妹、小妹绣花。大妹有耐心儿,小妹没绣几针,就到一边儿“抓子儿”去了。
小姨很累,大事小事都得操持,姥姥心疼,和西关老舅商量,接老舅的二闺女小鸾来家帮小姨照料我们兄弟姐妹,两位小姨是家里最忙的人。
姥姥让小姨张罗弟弟“抓周”的事儿。
小姨摸透了姥姥的心思,在炕上摆了几样物件儿,一管七紫三羊小楷笔,一盒香粉,一架紫檀算盘,一枚“光绪通宝”铜钱,一碟儿槽子糕。小姨把那管毛笔放在弟弟手底下。“抓周”开始,弟弟就近抓起毛笔,姥姥高兴了,说,我就知道这小子有出息,长大了念书,中状元,骑马坐轿……姥姥话音儿刚落,弟弟伸手抓起一块槽子糕捂在嘴上。母亲笑了,一屋子人都笑了。小姨说,原来是个“馋嘴状元”。
熏风习习野荷香
幼承家教,五岁发蒙,六岁学书,父亲为我写描红仿影: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
父亲并不析讲诗意,只是把怎样起笔,如何藏锋,以及“点点儿如桃,撇撇儿如刀”的习字格言说给我听。这小诗,合辙押韵,朗朗上口,描了几遍,不仅能背诵,还朦朦胧胧悟出一些诗意呢!
父亲是我的文学启蒙师。
父亲工笔书写的“仿影诗”,是我最初的文学读本。
大山哥、喜群哥、吉辰哥、锁成舅、福寿舅,常带着红瓤山药、面北瓜来家看我姥姥。给我带来的是文化乐趣。
大山哥给我唱“苏武留胡节不辱,雪地又冰天,穷愁十九年。渴饮雪、饥吞毡,牧羊北海边……”
喜群哥在北平念书,给我讲金銮殿。
吉辰哥让我猜字谜:“一点一横长,梯子顶住梁,大口张开嘴,小口里边藏。”
锁成舅给我唱:“怒发冲冠,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……”
福寿舅给我念街头墙上的帖子: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个夜哭郎。行人君子念三遍,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
小城南门里有一条通衢大街,大街上有一所龙冈书院。父亲说,龙冈书院是康熙年间栾城知县王巩创建的。父亲打开《栾城县志》给我看,说王知县是一位“实心实政积于学道”的县太爷。王知县写过一篇文章,说“为令者何敢不讲学以自励、励人?”王知县离任时,写了一首诗,夸龙冈书院是“百年轮奂丕基新”;夸龙冈学子“任重从来贵凤麟”;感叹“为愧匆匆分手去”,结句“青云端望此中人”,期望邑庠子跳龙门,上青天。父亲这些话,我听不懂,但隐隐约约觉得这位县太爷,有学问,是个好官儿。
清末,西学东渐,龙冈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。
我在龙冈书院读小学四年级时,寺上村翟文山先生任教。当时,翟老师二十出头儿,北京美专毕业。翟老师是严师。一天,翟老师板书《陋室铭》,让我们用工笔小楷写下来。老师并不析讲字指,考论文义,只是领着我们一遍又一遍高声诵读,于是,教室里一片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……学了《陋室铭》,又学《爱莲说》《习惯说》《归去来辞》《桃花源记》《五柳先生传》《大铁椎传》,依然是抄写、朗读,读着,读着,诸如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“悟已往之不谏,知来者之可追”“不戚戚于贫贱,不汲汲于富贵”等句,便烂熟于心。
课业之外,我迷上“闲书”:《西游记》《杨家将》《包公案》,逮着什么读什么。一次,回西宫,从堂哥的书箱里翻出一本外国人写的书:《爱的教育》,是一个男孩儿的日记,读起来没有“拦路虎”,不像《西游记》那么多生僻字儿。我把《爱的教育》拿到班上,向同学显摆,翟老师看见了,我心里敲小鼓儿,怕被没收。翟老师拿起,翻了翻,没说什么。从此,我的胆子更大了,读《鹰爪王》,读《粉妆楼》,读《呼延庆打擂》……一头扎下去,直读得风生水起。
我们作文用毛笔。翟老师命题,让我们写夏夜,写雪景,写庙会,写祭孔。我写得投入,每次看到老师的红笔圈点,便沾沾自喜。
栾城四门,嵌有石刻阴文擘窠大字。东门曰:眺旭;西门曰:映霞,南门曰:迎薰,北门曰:拱极。我看不懂,默记在心。栾城城内,有一座戏楼,灰瓦敞厦,翼角飞檐。后台粉墙上,有伶人留言:隆庆班在此作场、庆余社在此作场。我看不懂,默记在心。我和弟弟喂着几只鸽子,给鸽子起了好听的名字:红嘴白、飞毛腿、翻毛菊花顶。我写日记:把“四门城楼大字”“戏楼粉墙留言”、鸽子的花名都写进日记,翟老师阅后,批个“甲”字。
翟老师为我作“疏枝墨梅”,书柳公权选字帖。我的毛笔字有了长进。春节时,父亲请子龙庙和尚写大门春联:敦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父亲写庭院照柱春联:云霞出海曙,梅柳渡江春。我写土地龛联:鹤发庞眉千秋古,龙须彩杖万世新。
翟老师会唱二黄。我喜欢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,好听。我记住了几句,回家便扯着嗓子唱:我主爷起义在芒砀,拔剑斩蛇天下扬……日里萧何荐良将,但愿得言听计从,重整汉家帮,一同回故乡……唱着唱着,竟对月下追韩信的萧相国生出几分敬仰之情。
翟老师打篮球。一边奔跑,一边喊“my ball!”“long 球!”我问老师“my ball!”“long 球!”是什么意思?老师看看我,没回答。却说“孺子可教矣”。我听不懂。后来才知道,老师喊的一句是英语,一句是中西混合语,意思是:我的球!传长球!后来才知道,老师见我“好问”,说“孺子可教”,是用司马迁在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中的话夸我:你这个小子是可造就的人才!
初小毕业,考入西门里高等小学。离开龙冈书院那天,翟老师给我们上最后一课,和我们同唱:熏风习习野荷香,离别本寻常。骊歌一曲送君别,愿君勿相忘……
这年,我十二岁,一个混沌初启的垂髫少年。